那深深地藏在童年记忆里的春夏秋冬
童年四季春
春天是百花盛开的季节。
小时候最先看到的春花是杏花,紫红红的、粉红红的、粉白白的,一朵一朵、一片一片地绽放在道路的边上、水塘的岸上。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不知道杏花是如何就这么突然地冒出来了,因为它们是在连续刮了三天三夜遮天蔽日的沙土大风之后一下子盛开在枝头的。
大风是突如其来的,而且来势汹汹,夹裹着黄沙铺天盖地地咆哮着,仿佛是天上的黄河决了口,洪水全部倾泄到了大地上。放眼望去,天地间看不到别的,只有横向飞舞的沙尘,打在脸上生疼。记忆中的杏树还是干枯枯的样子,树干和枝叉显得那么苍老和无力;谁知就在大风停了的时候,杏树的枝头突然变成了花的世界,杏树林里突然变成了美的海洋。
沙土大风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杏花开放?虽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但杏花已经开了,所以我们没有心情再去理会和琢磨别的事情,而是纷纷跑向杏林,爬树的爬树,折枝的折枝,最后都手举几枝杏花跑回家中,插进瓶子里,倒进水去,然后静静地等着枝上的杏花全部开完。
春天,就是在大风和等待中到来的。
大点的孩子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大人们也都背起农具赶上牲口下地去了。
田地里还是不时地会刮阵小风,会刮起枯草,也会刮起尘土。尘土飞进嘴里,轻轻一咬,“格格”作响,好像熟沙了瓤的西瓜一样。尘土落到田里,落到早已调好的沟畦里;沟畦里的水已经渗下去了,沙尘落上去就像洒了一层白糖,然后又慢慢溶化掉了。
大人们从附近担水浇灌的时候,我们则拿着小碗或小杯跑到路边上去做土馒头。做土馒头的土不能太干,太干了容易散,成不了形;也不能太湿,太湿了就变得又软又粘,不光滑。选择松软的地方挖去浮土,取用下面的新土来玩。新土的颜色深,气味鲜,手感也好,挖出来装进碗里,装填得满满的,再使劲把碗面儿压实,把碗沿儿抹平,然后把碗快速地倒扣在地面上,轻轻地敲打几下碗底儿,再慢慢把碗旋转几下,里面的土就和碗分开了。小心地将碗提起来,一个浑圆饱满的“馒头”就做成了。瓷碗、酒盅都可以做土馒头,什么形状做出什么样的馒头,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各式各样的土馒头摆在一起,真是好看。
大人们经过时就说:“做了这么多,你们晚上就吃这些馒头填肚子好了。”
我们也玩够了,就抓过点种子放到刚才的碗里,“帮”着往浇过水的沟畦里点种子。
那时种子的发芽率不高,为了将来苗能出得全,大人们往往要点上5至7粒种子,有时可能还要更多。即便如此,也不能确保百分百地出齐了苗,很多时候需要进行二次补苗才行。点好种子,盖上浮土,有条件的还会罩上一层薄膜,这时的田野就好看多了,一道道脊垄好比一条条金龙银龙,它们整齐地伏卧在大地上,就像古代的军队摆下阵式要开赴战场一样,壮观极了。
出苗以后,只有少数地段需要进行补种。钻出土来的小苗儿挤在一起,在风中争相向世界展示着自己。大人们会薅除弱小的苗子,只留下23棵长势好的;被拔下的小苗儿无助地躺在那儿,根儿上还带着湿湿的泥土。每当这时,我就倍加感到心酸和难过,同时也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大人们要栽种上它们赋予它们生命,到头来却又残忍地亲手扼杀它们。我跟在大人身后,会偷偷把其中一些苗儿的根再小心地埋进土里,想到它们能活下去了,心中就感到一丝慰藉。记得小人书中林黛玉葬过花,可能她也有这种悲天悯物的情怀吧。
风沙越来越少了,天气越来越热了,庄稼也长得越来越高了。人们一边忙着麦田,一边忙着棉田;除了浇地、除草,还要打药灭虫蚜。绿叶和红花渐渐在我们眼里失去了新意,我们转而搜寻其他的乐趣,最喜欢玩的是“瞎瞎撞找媳妇”。
大人们在地里劳作,我们就在一边挖土,不过这次不是做土馒头,而是寻找“瞎瞎撞”。它是一种和瓢虫差不多的小虫,有漆黑的,也有棕褐色的。先从土里挖到一只瞎瞎撞,然后在不远的地方挖个坑,填上点新土,做成一个比较松软的“新房”,再把刚才挖到的瞎瞎撞放进去,埋上新土,不轻不重地拍打结实。这下,有了新房的瞎瞎撞就成了新郎,它就会找来另一只瞎瞎撞当媳妇,或者会有另一只瞎瞎撞主动过来给它当媳妇,如果这时再把“新房”挖开,就会有两只瞎瞎撞了。那时我们玩这个乐此不疲,玩上一会儿,手里就攥满了瞎瞎撞,它们爬来爬去,弄得手心里痒痒的。我们就把黑的放了,只留下颜色好看的。黑色的瞎瞎撞张开翅膀,露出来白白的肚子,东一头西一头乱撞着飞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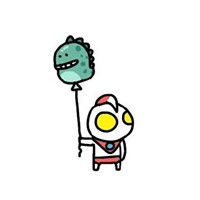
浮生
本文链接:https://u1e.cn/tweet/8511 [复制]
相关推荐